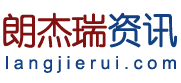「价值链中国」什么是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我国处于什么位置)
今天,神州网给大家普及下关于「价值链中国」什么是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我国处于什么位置)的知识。
最近几年,随着价值链在全球扩展,新的贸易方式已经诞生。
以美国苹果公司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利用全球价值链战略,把产品的制造和组装外包给合同加工商,自己则专注于产品设计、推广和销售。这种贸易方式不同于传统贸易,目前的贸易统计无法追踪这种新的贸易活动。
例如,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中国2018年仅从美国进口了400万美元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而事实上,仅苹果一家公司就在中国销售了520亿美元的同类产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矛盾的现象?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的海外院长邢予青认为,这样的误差与过时的统计方法有关。如今沿用世界银行对价值链贸易的定义过于侧重出口产品中使用的进口中间品的比例,它漏掉了部分沿价值链的贸易活动。
如果根据世界银行对价值链贸易“跨越国境两次的中间产品”的定义来计算,2010年到2020年,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从35.1%下降到33.9%。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很多原本进口的原材料,中国都可以生产了,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为知名品牌代工,品牌方出无形资产(创意、设计等),中国负责组装生产。随着国内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代工产品在中国完成内销,并未发生实物进出口行为。
在邢予青看来,这样的交易,应该未被计算到全球价值链的统计范畴,且这类贸易数额巨大。如果使用新的计算方法——“要素收入贸易”概念来计算,就会发现2005年-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比传统计算方式平均下降32%,比现在流行的增加值贸易的算法下降17%。
那么,全球价值链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全球价值链为什么能够促进中国的出口?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如何?针对全球价值链的诸多问题,《财经》记者近日专访了邢予青教授。
《财经》: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全球价值链正在发生断裂。您怎么看?
邢予青:断裂一词用得过于夸张,但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价值链中断是事实,这体现在生产与运输两个方面。生产方面,武汉封城时工厂停工,导致日韩下游汽车公司停工,这是价值链中断的一个体现。第二个例子是口罩生产。2020年1月,中国台湾宣布禁止口罩出口,结果,在台湾的新加坡ST科技公司,无法把生产好的口罩运回新加坡,导致新加坡出现口罩短缺。欧洲、加拿大需要从美国进口3M口罩,但是,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动用“战时法案”禁止口罩出口。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导致全球口罩需求急剧上升,但口罩生产和出口却因为防疫措施而中断。类似的情况,酒精、洗手液、呼吸机等供应链也有中断现象。
截至今天,美国洛杉矶港口还有很多积压的货柜。如果美国企业不是按照价值链的方式从事进口与生产,而是在国内生产这些产品,就不会存在货柜积压的问题。
美国的跨国公司在过去几十年一直进行去工厂化,侧重于产品的研发、设计,以及产品的批发和零售,把产品的制造和组装工序都放在海外,特别是中国,这就导致了对产品跨国运输的需求。疫情扰乱了海运和航空运输,美国的港口也缺少卡车和工人。
《财经》: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的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制造企业回归,以完善本土化供应链能力和经济的独立性,这是否会把中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
邢予青:我在《解码中国出口奇迹》一书里写到,目前有两个阴影笼罩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上。
一个是目前依然流行的新冠疫情。防范病毒的防护服、口罩、消毒液、呼吸机等这类产品的制造,已经标准化。发达国家去工厂化后,将这些产品都放在海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中国居多。疫情暴发后,许多发达国家才突然认识到自己缺少生产这些基本医疗物资的能力,面对疫情想多生产也没生产设施。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药原料最大的出口国。新冠疫情刚暴发时,印度有一段时间禁止药品出口,因为这些药品的制造依赖中国生产的药原料。
另一方面,在全球价值链上负责生产这些紧缺医疗物资的国家,由于也受到疫情的冲击,就优先考虑将紧缺的医疗物资应用于本国的防疫。这样一来,制造好的防疫产品就不可以按照原来的计划出口。这就是为何一些外国评论家说: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突然变成了Used in China(中国使用)。当然,对于政府来说,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时,优先保护本国居民健康是无可厚非的。
为了防止今后出现类似的问题,许多国家已经提出要加强本国生产基本医疗用品的能力,并鼓励企业把医疗用品生产线搬回本国。例如,日本政府就提出,如果日本企业将与健康相关的供应链从中国搬回日本,分散到东南亚,或者南亚,日本政府就给补贴;如果日本企业在国内扩大药原料的产能,日本政府可以补贴50%的投资。
美国政府2021年6月发布报告:“建设有韧性的供应链,复兴美国制造业,实现全方位的增长。”这个报告指出,美国87%药原料需要进口,这会导致美国在危机时出现药物短缺的危险,要求加强美国基本药物和药原料的生产,并要求美国联邦政府下属机构在采购药品时,优先采购美国造的药。这些做法显然会导致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重要作用。
《财经》:除了医疗健康领域,在其他领域,跨国公司会不会加速生产线撤离中国的步伐?
邢予青:疫情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实际上是与中美贸易战叠加的。中美贸易战始于2018年3月,疫情开始于2020年1月。现在中美贸易战还没有结束,美国对中国产品增加的25%关税还没有取消。
中国有一个“世界工厂”的美誉,这个世界工厂的最大的客户是美国。在我主编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超越制造》中,我们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网络的演变。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是目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中心;但从需求的角度来看,美国一直是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这一事实说明,美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跨国公司从中国采购商品,在中国制造,或者组装产品,然后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节约产品的制造成本,获得更高的利润。但是,美国对中国产品施加的25%关税,足以抵消这种价值链运作带来的全部利润。这25%的关税成本,无论是由中国制造企业负担,还是美国进口企业支付,长期而言都会迫使这些企业作出调整,从而影响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避免25%关税成本,是一些跨国公司将服务于美国市场的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中国的歌尔股份为苹果公司组装AirPods,AirPods现在属于被征收25%的关税的产品。为了避免这个关税,歌尔股份已经将AirPods组装厂搬到了越南。
《财经》:不久前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提到,世界经济中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已经上升到44.4%,但是,中国的参与度与2010年相比却下降了,为什么?
邢予青:我们的报告使用的一个指标显示,从1995年至2020年,世界各国总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从35.2%上升至44.4%。但是,中国的参与度却从2010年的35.1%下降到近期的33.9%。这的确是一个有意思的结果,和大家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直观印象不太一致。
我认为这与参与度的定义有关。参与度指数是根据世界银行对价值链贸易的定义来计算的。世界银行把价值链贸易定义为跨越国境两次的中间产品。这个定义是非常狭隘的,它漏掉了许多沿价值链的贸易活动。由于它侧重于出口产品中使用的进口中间品的比例,那么,随着中国企业的生产和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很多原来进口的原材料中国都可以生产了,这个指数自然就会显示出中国价值链参与度下降了。
根据我的估算,中国组装的第一代苹果手机的96%制造成本来自进口零部件;到了iPhone X,进口零部件下降为制造成本的75%,根据这个算法,中国企业参与苹果手机价值链的程度,就大大降低了。这个结论显然是错的,因为中国的苹果手机出口显然是参与苹果公司价值链的结果,有更多的中国企业给苹果提供零部件,说明中国企业参与度是增加而不是减少。
从出口量来看,2009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大约1300万台苹果手机。2018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大约4200万台更贵的苹果手机,因此,中国企业参与苹果手机价值链的规模是更大了而不是缩小了。
另一方面,以出口的中间品为基础的价值链参与指数,完全忽视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价值链活动,例如,在中国销售的特斯拉电动车和苹果产品,显然都是依赖全球价值链制造的,但是,它们都是从中国的组装厂进入中国市场的,一次边境也没有跨越,这些经济活动显然就被“跨越边境两次”的定义排除在外了。
我们这期报告的主题是“超越制造”,意思就是,如果要理解全球价值链,就要“超越制造”这个环节。全球价值链实际上是一个产品,从构思、研发、零部件制造,到组装、批发、零售,一个产品全部价值生产的链条,而现有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的测度,仅侧重于制造这一个环节。
2021年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的贡献之一,就是对传统的方法进行了扩展,把跨国公司的内销产品,以及出口的最终产品,都算作全球价值链的活动,根据这个新方法,我们发现全球价值链对于GDP的贡献成倍增加。例如,按照出口中间产品为标准的测度,2016年全球价值链对GDP的贡献只有10%;把跨国公司的活动包括在内后,我们发现全球价值链对GDP的贡献是20%。
《财经》:如果用“要素收入”来计算中美贸易平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可以下降32%,如何理解这种算法?
邢予青:美国的许多跨国公司利用全球价值链,把产品的制造和组装外包给合同加工商,自己专注于产品的开发、设计、品牌推广和零售。它们开发产品、销售产品,但是,并不参与产品的具体制造,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无工厂制造商。
这些无工厂制造商已经不再从事把“美国制造”的产品卖给中国消费者的贸易活动了,而是把“中国制造”“越南制造”“印度制造”等贴有自己的品牌和包含自己的专利技术的产品,销售给中国消费者。通过这种方式,它们获得的是属于自己的无形资产,例如品牌、专利技术、软件、供应链管理等等的收益,这是随价值链在全球扩展战略衍生的一种新的贸易方式。这种贸易方式不同于传统的服务贸易,目前的贸易统计是无法追踪这种新贸易活动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微软将Windows操作系统的使用权许可给中国的联想公司,联想公司需要给微软支付使用费,这笔费用就会被贸易统计列为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但是,苹果公司并没有将它的操作系统许可给任何一家制造商。它是通过把由自己研发和设计、由富士康组装的电脑卖给中国消费者,来获得自己研发的操作系统的收益。这笔收益,就没有被算作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
根据我的估算,2018年美国四家无工厂制造商——苹果、耐克、高通和AMD,从中国市场上获得279亿美元属于它们的无形资产收入。这279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官方统计的美国对中国服务出口的50%,远远超过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或者波音飞机的数额。如果这279亿美元被计算为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2018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会减少7.5%。
除了无工厂制造商,还有一些美国的跨国公司是通过直接投资,从中国的市场上获得自己垄断的无形资产收入。例如,美国特斯拉和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已经让国界在定义贸易活动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因为跨国公司可以从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向国际市场出口产品,没有必要非要从自己的母国向国际市场出口产品。
为了估算一个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实际出口,我们引入了“要素收入贸易”概念,把一个国家的出口定义为这个国家拥有的要素,基本就是劳动力和资本,从国际市场上获得的收入,无论这些要素是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
用这个概念,我们重新估算了2005年-2016年中美两国的贸易平衡,我们发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比传统计算方式平均下降32%。比现在流行的增加值贸易的算法要下降17%。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的跨国公司通常利用极其复杂的会计方式,把无形资产转移给海外的分公司,例如苹果公司的无形资产基本属于它在爱尔兰的分公司,因此,“要素贸易收入”的计算里,并没有包含美国无工厂制造商对中国的出口。如果包含这一部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的下降,会远远超过32%。
传统的贸易概念和统计已经过时,我们必须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状,这样才可以科学的估算两国贸易不平衡的真实现状。
《财经》:全球产业链越来越长,世界各国分工细致,这对于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来说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分工越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会的同时,是否也使它们被锁在增加值的最低端?
邢予青:这个问题在学术上被称为“低增加值陷阱”。有一些研究发展的学者对全球价值链持有怀疑态度。
在2021年12月13日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超越制造》的发布会上,世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库普曼就说,他2014年刚到世贸组织时,人们不愿意讨论全球价值链,认为那是跨国公司用来剥削发展中国家的策略。但是,现在大部分学者和决策者对待全球价值链的态度已经改变。这期报告发布后,印度政府对印度IT产业如何实现价值链升级,非常感兴趣。
我一直认为,全球价值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件好事,它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提供了一种新路径,是发展中国家跨越市场壁垒和技术壁垒,分享全球化果实的一种捷径。
以中国为例,我认为中国企业积极深入加入全球价值链,是中国创造出口奇迹的关键。中国过去4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不同于以韩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奇迹。日本和韩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它们拥有独立的品牌和技术。
但是,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的企业并没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哪怕是在最有比较优势的衣服和鞋方面。手机和计算机品牌,也是近几年才出现。作为世界第一高科技产品出口大国,中国企业并不拥有这些出口的高科技产品的核心技术的产权。但是,这些缺陷并没有阻止每年2.5万亿美元的“中国制造”产品进入世界市场,哪怕是竞争最为激烈的发达国家的市场,中国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是“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上成功的秘诀。
一般而言,加入全球价值链后,中国的企业就可以享受三个溢出效应,第一个就是跨国公司拥有的国际知名品牌的溢出效应。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在于劳动力廉价、产品价格便宜,这是不对的。我们服装出口量之所以高,是因为我们给耐克、Zara、优衣库等知名品牌代工,如果在国际市场上卖国产品牌的衣服,服装出口绝对不会是世界第一的。大部分消费者买东西时,具有非常强的品牌导向,产品没有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就没有认知度,就没有销量。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第一障碍就是品牌。而一旦中国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成为跨国公司的供应商,它们无需担心品牌的问题,例如,大家对耐克鞋的喜爱,最后就变成了对“中国制造”的耐克鞋的喜爱,这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品牌溢出效应。
第二个溢出效应来自于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的研发和产品更新。任何一个先进的产品,除了需要核心技术部件,例如芯片、操作系统等等,也需要低技术含量的标准零部件和劳动密集型的组装服务。中国企业通过提供标准零部件和组装服务,就可以享受由价值链主导企业技术革新引起的对新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例如,中国的立讯精密和歌尔股份是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当苹果公司通过研发不断推出新款苹果手机时,全球消费者对新款苹果手机的需求,就自然转化为对这两家中国公司制造的零部件,以及组装服务的需求,从而带动它们的出口。
第三个溢出效应来自于价值链主导企业的全球批发与零售网络。优衣库大约90%的合同制造商都在中国。优衣库在全世界开的店越多,中国的供应商就可以向全世界的消费者卖出更多的T恤衫和牛仔裤,但是,中国的企业并不需要为优衣库开设的这些店铺投资一分钱。
不仅中国的企业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获益。印度的软件产业、菲律宾的商务外包产业,都是全球服务产业价值链的一部分,都得益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2021年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专门介绍了印度和菲律宾加入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成功经验。
《财经》:中国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下游,如何向价值链更高端跃升?
邢予青:从微笑曲线来看,研发、产品设计、品牌、批发或者零售,是任何一个产品的增加值的高端。中国是通信和信息技术产品出口的第一大国。中国笔记本电脑出口全世界第一,占全世界出口的75%;手机出口全世界第一,占世界出口的56%。但是,我们的报告利用微笑曲线对中国的通信和信息技术产品分析发现,中国的企业基本处于标准零件制造和组装这些低增加值的区域。
但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进入增价值相对较高,技术相对复杂的任务领域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例如,在第一代苹果手机中,中国企业贡献的增加值,只有全部制造过程的3.6%。到了iPhone X时代,中国企业贡献的增加值,已经达到了全部制造过程增加值的25%,和韩国企业的水平一样,并且已经超过了日本企业对苹果手机增加值的贡献。
打造国际知名品牌,是获得高增加值来源的一个重要手段。拥有品牌也是成为价值链主导企业的一个充分条件。中国的小米手机和OPPO手机,已经成为了价值链的主导企业。这两个品牌手机的国内增加值,大约在45%左右,品牌收益是这两个品牌手机国内增加值大大超过苹果手机国内增加值的主要原因。
在《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中,我们提出了沿价值链升级的两种路径:线性升级和非线性升级。侧重产品制造技术的企业,可以遵循线性升级的路径,华为公司就是中国企业中线性升级的代表;侧重于市场营销和品牌的企业,可以走非线性升级的路线,联想集团就是沿价值链的非线性升级代表。这两种策略都需要企业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目标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