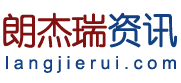「名节东汉」盛女的黄金时代剧情(盛女的黄金时代插曲叫什么名字)
最近很多人在问「名节东汉」盛女的黄金时代剧情(盛女的黄金时代插曲叫什么名字),今天神州网就「名节东汉」盛女的黄金时代剧情(盛女的黄金时代插曲叫什么名字)展开分析。
本文转载自 宁胡阏氏 在公众号的原创文章,已经得到作者授权。
一、名节
话说:汉魏之士多重名节,然而知名节却不以礼法加以节制,遂至于苦节。故当时名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发展到极致,就是魏晋之士的旷荡,尚浮虚而亡礼法,此即为诞节(荒诞的名节)。
这句话揭示了东汉—魏晋间,士风转变的过程及原因:名节之极而至苦节、苦节之极而至诞节。然而尚须追问的是,名节为何要“至于苦节”,苦节又为何要趋于“极”,而变得荒诞呢?如果先说结论的话,它与汉代的察举制度有关, 这是汉魏士风及其主体转变的内在原因。
自西汉武帝尊崇儒术,特别是好儒的汉元帝之后,经学大盛,儒生日多。汉成帝时太学生,增弟子员三千人。东汉光武帝爱好经术,明帝亲临太学典礼,至顺帝时,游学增盛,洛阳的太学生多达至三万余人,占据洛阳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郡国学生尚不在其内。民间经师开私学授徒,“传业者浸盛”,门生数量众多,或“编牒(学生名册)不下万人”,如汝南蔡玄门下,“其著录者万六千人”。
但是,儒生的出路只有学优而仕一条,开门授徒也不过是这一条道路的延伸。而东汉中后期, 在太学乃至私学习业的儒生,总数以十万计,都挤在入仕这一条独木桥上,竞争的激烈程度可以想见,可谓“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东汉中后期又恰是宦官专权的时代。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占去大量职位,从而使士人向上流动的通道变得更加狭窄,也使士大夫集团与宦官势力的矛盾更加激化,这也是党锢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
然而促使士风改变的根本原因,还是士林内部的竞争。经学之盛,汉代选举以察举为代表,察举又以孝廉为主,秀才(茂才)次之。但不管哪一科,都需要通晓经学才行。“通一艺以上”是儒生(诸生)入仕所必经的考试,东汉顺帝朝的“阳嘉新制” ,“通家法” 即考试经术始成为察举孝廉一个必经环节。
孝廉本为儒家伦理的实践,故察举孝廉的中心环节还是郡国举荐,举荐的重点则在德行,即孝悌与廉让。总之,汉代选举的主要标准,按照当时的术语就是“经明行修”。“经明”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其成绩也便于考察 。“行修”则取决于他人的观察和评价。
因此宗族乡党的批评,道德所施对象的评价,也就是所谓“乡里清议” 、“乡论”,就成为选举上最重要的凭藉和标准。郡国对孝廉的举荐,其根据就是被举荐者在乡党的名望,可见“行修”要取得好的成绩,实取决于名望 。
范晔在《后汉书》论“东汉之所谓名士者:“刻情修容”。所谓“刻情修容”就是矫揉造作以表现“行修”,以博取名望,高抬身价。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博取名望,这样的名士并不能通达事理 、应付时需 。
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行修”,具体体现为礼教或曰名教,包括小至言行举止的中礼,大至对三纲五常的遵循。当时太学诸生,有专门的服装,要学习矩步。《儒林列传》中的:沉静乐道,举动都很讲究礼。他的学生周燮:志行,非礼不动,对待自己的妻子像君臣那样恭敬。
礼之大者莫过于丧礼,鉴于“生孝”难以考察, 故服丧便成为孝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西汉成帝时代,少有依礼行三年丧者,但到两汉之际特别是进入东汉后,行三年丧的就多了起来。
汉光武帝时“雅称儒宗”的韦彪,《后汉书》称其: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寑 。守孝完毕,他整个人变得羸脊骨立异形,调养疗愈了好多年才恢复健康。他后来“举孝廉”可谓名副其实。至迟在安帝时行三年丧已普遍化,其后士人为了在“行修”上有异常表现,于是有突破之举。
汉安帝时汝南薛苞, “丧母,以至孝闻”,父及继母死后,又“行六年服,丧过乎哀” ;苞与其侄分家时,奴婢只要老朽的,房子田产只要破败的,东西只要破烂的。廉即让,让名让财,薛苞真是既孝且廉,后来拜官,“受禄致礼” ,乃实至而名归。
宗室东海王臻,以及袁绍都是服丧六年,因父死时年幼,长大后又补服三年。又有为长官、、恩师制服守丧者,为同僚、同窗千里奔丧者。让爵让财者,亦多不胜举,如乡侯邓邯死后,其子邓彪让其爵位于异母弟邓凤,张禹父卒后,以田宅让其伯父,韩棱以父财数百万让给从弟韩昆。
以上都是对儒家丧礼和汉代法定爵位、财产继承方式的突破。赵翼《廿二史札记》:“东汉尚名节”条将这种现象与当时的选举制度联系起来:当时的察举制,主要看重人的名誉,所以只要有利于树立名誉的事情,大家都争相去做,标榜自己,以致于形成攀比的风气。
其实东汉人应劭《风俗通义》中,就针对这类现象进行批评。他指出,当时有人在母亲、兄弟死后不归家服丧,却为长官、举主服丧,难道“真不爱其亲而爱他人”吗? 实因后者都是名门,达官贵人,争相献殷勤和攀附,就是希望以后在仕途上得到奥援,在社会上获得名誉。
当时的士人认为,虽然“过”了一些,儒家本强调中庸,“过犹不及”,但儒家又有“观过知仁”之说,故还是宁左勿右保险,宁过而唯恐不及。对礼的突破既根源于要在“行修”上出奇制胜,以获得作为察举凭藉的名誉,于是这种突破就有类于打破纪录的体育竞赛,为破纪录而百计千方,同时也一如体育竞赛,难免出现虚伪和作弊 。
东汉服丧上的最高纪录是桓帝时青州乐安郡人赵宣创造的。他“为父母服丧二十余年”,以墓道为居室,“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太守陈蕃听到他的模范事迹后,亲临访问,方知他在所谓的服丧期间,连续生育了五个子女,这是严重违反丧礼的行为,遂大怒而“致其罪”。
因为依礼服丧, 衣食、住行、起居皆有严格规定,三年下来,大抵如上举韦彪,“羸脊骨立”,不成人样,“医疗数年”才能康复,死于服丧中的不乏其例。这是孝的作伪。据《后汉书·许荆》:许荆的祖父许武被举为孝廉后,考虑到两个弟弟还未出名,就“共割财产以为三分”,而“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从而为两个弟弟博得了“克让”也就是“廉”的名声,均被察举为官。
若干年后, 许武又召集“宗亲” ,哭诉当年分家时自己多占财产,是为了弟弟们的前途, 并且又将自己业已增殖的财产“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 。而此举又为许武博得了更高的声誉, 因为过去贪财是为了弟弟当官,是“孝悌”,现在将财产送给弟弟,是“廉让” ,于是“远近称之”,官升至“长乐少府”。显然,这两次财产分割,都是有预谋的操作、炒作、矫揉造作,是廉的作伪,也是孝悌的作伪。
这种的社会风气发展到魏晋之际,则演变为诞节、旷荡。
二、诞节
《风俗通义》卷四《过誉》:
江夏太守河内赵仲让 ,举司隶茂材, 为高唐令 。为郡功曹所选 ,颇有不用 ,因称狂 ,乱首走出府门。太守以其宿有重名 ,忍而不罪 。后为大将军梁冀从事中郎, 冬月坐庭中 ,向日解衣裘捕虱, 已,因倾卧 ,厥形悉表露。将军夫人襄城君云 :“不洁清 ,当亟推问 。”将军叹曰 :“是赵从事, 绝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洪范》陈五事,以相貌为首;《孝经》列三法,以服饰为先。衣冠 、冠带,本是儒家礼乐文明的象征,因而成为官吏、士人的代称。东汉太学生的典型形象,就是“方领” 、“长裾” 、“矩步” 、“进止必以礼” 。
然而这个赵仲让却“乱首”“ 称狂”,甚至于当众裸体,这是对当时名节、苦节的反动,并开魏晋名士刘伶 、王澄 、谢鲲、胡毋辅之、阮放 、光逸等“散发裸裎” 、“裸体” 的先河。而且赵仲让“宿有重名”,甚至连执政梁冀都任其狂放,也许梁冀认为,别人裸体自然是失礼,但对于“绝高士”的赵仲让来说,不过是演绎其高情逸致的“行为艺术”而已。表明士林风气及评价标准正在悄然生变 。
《后汉书·袁闳传》:闳“少励操行,苦身修节”。其父任彭城相,他在“省谒”的来往途中,包括在彭城郡界,“变名姓,徒行”,既不肯暴露郡相之子的身份,又不肯坐父亲给他派的公车。后来其父死于任上,他去迎丧时“不受赙赠”(按照当时惯例是很大一笔钱)。他还拒绝身居高官的叔父袁逢 、袁隗的赠馈 。这是绝对的廉让,到了不近人情的“苦节”地步。
袁闳在护父丧途中, “缞绖扶柩,冒犯寒露,体貌枯毁,手足血流,见者莫不伤之”,是一种恪遵丧礼到令人感动的至孝。然而同样的袁闳,当后来党锢之祸时,袁闳却不著冠服。“散发绝世”, “筑土室”自居。其母亲死后,他竟不穿孝服、不设母亲灵位,与他父亲死时所表现出的至孝绝然不同 。
东汉初年以来,由三年之丧而六年而二十余年,以至服丧期间饮酒食肉,在丧礼上完成了由苦节向诞节的转变 。时人无法适应诸如袁闳那样的由“苦节”一转而至“旷荡”,故称闳为“狂生”,认为他精神错乱了。实际上这是由于袁闳对自己过去所坚持的价值观(名节 、苦节)也丧失了信心。这样的“ 狂生” 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无独有偶,比如列于《后汉书·独行列传》的向栩:喜读《老子》、披头散发,不著士服,长啸(歇斯底里的大叫),以及当官而不任事,这些都是之后魏晋名士的行事特征 。而且这种变化不仅仅限于外表、行为 。
《后汉书 ·逸民列传·戴良》 :
字叔鸾 ,汝南人也。少诞节 ,母喜驴鸣, 良常学之以娱乐焉 。及母卒 ,兄伯鸾居庐啜粥 ,非礼不行 ,良独食肉饮酒, 哀至乃哭, 而二人俱有毁容 。或问良曰 :“子之居丧 ,礼乎 ?” 良曰:“然 。礼所以制情佚也 ,情苟不佚 ,何礼之论。夫食旨不甘 ,故致毁容之实, 若味不存口 ,食之可也 。”论者不能夺之 。
此即为“诞节”,《汉书》卷四十《叙传下》:“诞节,言其放纵不拘也 。”“任诞”,也就是“旷荡”。
戴良之学驴叫以娱其母,岂不是与西晋名士孙楚,因王济生前喜爱孙楚作驴叫,故在王济的灵前,维妙维肖地作驴叫相似么?重要的是戴良母亲过世后,其兄伯鸾仍恪守丧礼,戴良却吃肉喝酒,而且悲伤起来就哭,于礼该哭时未必哭。这些都是严重的失礼,但他伤心憔悴(毁容)的程度却丝毫不亚于他依礼守丧的哥哥。
更重要的是他不认为自己失礼,其诞节行为自有其理论根据。他认为丧礼是用以限制那些缺乏人伦孝思、邪情荡佚者的,而他对母亲的孝思和哀伤由衷自怀,虽饮酒食肉,也符合礼。因为对他来说,酒肉吃在口里也是苦的,故身心憔悴。惟其如此,他可以超越礼的限制,包括饮食衣著方面的丧礼规定。
他直指礼的人伦本质,而不拘守甚至超越其外在形式,可视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先声。阮籍服母丧期间照旧饮酒食肉,葬母时,蒸一头大肥猪,饮酒二斗,然后临诀,举声大哭, 吐血数升,以致很久恢复不过来。实质上也是注重对母亲的天然孝思,而无视丧礼的繁文缛节。可以说,从理论到实践,“诞节”的戴良已无异于尔后“任诞”的魏晋名士,倘与嵇康、阮籍同时,他应是《世说新语》的合适人选,竹林也很可能不止七贤。
古书中谈论汉魏社会风气,有所谓“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苦节至极,则为诞节。”的说法,主要在于经学的兴盛激化了儒生数量膨胀,而选举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加上宦官专权,导致仕途竞争白热化,最终使察举制度诸要素变质 、异化,使得当时的士人们思想发生变态扭曲,人性压抑,与当初的目标预设相悖,最终变成沽名钓誉,标新立异,从而走向崩坏。